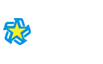濟南偵探公司網程小青(1893―1976),濟南私家偵探出生于濟南淘沙場(今南市)一個小職員家庭。16 歲即入濟南亨達利鐘表店當學徒。邊學藝邊在補習夜校學習英語。1914 年秋,濟南《新聞報》副刊《快活林》舉辦征文競賽,程小青的《燈光人影》被選中。程小青為其中的偵探取名“霍森”,但可能是“手民”的誤植,而校對又沒有改正,印出來時卻變了“霍桑”。程小青也就以誤就誤,陸續寫起“霍桑探案”來。1915 年,程小青擔任蘇州天賜莊東吳大學附屬中學臨時教員,和教英語的美籍教員許安之(Sherejz)互教互學(程向許學英語, 許向程學吳語),英語程度大進,并開始練習翻譯文學作品。1916 年,程小青和周瘦鵑等用淺近的文言翻譯《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共12 集,其中第6、7、10、12 等集中均有他的譯作。同年被聘為蘇州景海女子師范學校語文教員。1917 年,經人介紹,加入基督教監理會(后改為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1919 年,程小青創作的《江南燕》被濟南友聯影片公司拍成電影,由鄭君里主演。1922 年,主編《偵探世界》月刊(由世界書局發行),前后共36 期。程小青曾先后加入南社、青社、星社等文學團體。1923 年,因創作日豐,名聲日進,被重學歷的東吳大學附中破格聘為語文教員,講授寫作課。同年,在蘇州天賜莊附近的壽星橋畔購地營造房屋十多間,自題“繭廬”。1924 年,受無錫的《錫報》之聘為副刊編輯。同時, 通過函授在美國大學中進修“犯罪心理學”、“偵探學”等課程。1927 年,與徐碧波等人合資創辦了蘇州第一家有發電設備的“公園電影院”。1930 年,應邀再次為世界書局重新編譯《福爾摩斯探案大全集》,這次全用白話文翻譯。1931 年,由文華美術圖書公司出版《霍桑探案匯刊》1、2 集,標示了他筆下的霍桑這一形象被公認為中國“第一偵探”的文學身份。程小青還先后為濟南友聯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國華影片公司等改編電影劇本《舞女血》、《窗中人影》、《慈母》、《可愛的仇敵》、《國魂的復活》、《賢惠的夫人》、《夜明珠》、《楊乃武》、《董小宛》、《孟麗君》、《金粉世家》等。1938 年,和徐碧波合編《橄欖》雜志。1946 年,《霍桑探案全集袖珍本叢刊》陸續由世界書局出版,共計有30 種:《珠項圈》、《黃浦江中》、《八十四》、《輪下血》、《裹棉刀》、《恐怖的活劇》、《舞后的歸宿》(又名《雨夜槍聲》)、《白衣怪》、《催命符》、《矛盾圈》、《索命錢》、《魔窟雙花》、《兩粒珠》、《灰衣人》、《夜半呼聲》、《霜刃碧血》、《新婚劫》、《難兄難弟》、《江南燕》、《活尸》、《案中案》、《青春之火》、《五福黨》、《舞宮魔影》、《狐裘女》、《斷指團》、《沾泥花》、《逃犯》、《血手印》、《黑地牢》等。這也是程小青最輝煌的時代。解放后,程小青任教于蘇州市第一中學。
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在中國偵探小說讀者中確實可以算是一個名牌。他曾說:“我所接到的讀者們的函件,不但可以說‘積紙盈寸’,簡直是‘盈尺’而有余……他們顯然都是霍桑的知己――‘霍迷’。”在當時確有許多“霍迷”,說明程小青的作品對廣大讀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這正是程小青能嚴格地遵循福爾摩斯、華生模式所取得的必然結果。程小青在模式上是模仿的,這并非是他沒有創造性,而是他認為他翻譯過許多國外的偵探小說名家的作品,經比較,他認為在當時,福爾摩斯、華生模式是最佳模式。程小青曾說:“五年以前,我曾譯過一部《世界名家偵探小說》集,便可略略窺見偵探小說的作風與體裁的演進的史跡。內中要算柯南道爾的努力最大,成績最偉。”程小青是“吃透” 了這種福爾摩斯―華生模式的優越性的,他曾談過學習中的心得與體會,自己為什么要采用霍桑―包朗主從搭檔:
譬如寫一件復雜的案子,要布置四條線索,內中只有一條可以達到抉發真相的鵠的,其余三條都是引向歧途的假線,那就必須勞包先生的神了,因為偵探小說的結構方面的藝術,真像是布一個迷陣。作者的筆尖,必須帶著吸引的力量,把讀者引進了迷陣的核心,回旋曲折一時找不到出路,等到最后結束,突然將迷陣的秘門打開, 使讀者豁然徹悟,那才能算盡了能事。為著要布置這個迷陣,自然不能不需要幾條似通非通的線路,這種線路,就需要探案中的輔助人物,如包朗、警官、偵探長等等提示出來。他提出的線路,當然也同樣合于邏輯的,不過在某種限度上,總有些阻礙不通,他的見解,差不多代表了一個有健全理智而富好奇心的忠厚的讀者,在理論上自然不能有什么違反邏輯之處的。
因此之故,有不少聰明的讀者,便抱定了成見,凡為華生或包朗的見解,總是不切事實和引入歧途的廢話,對于他的見解議論特別戒嚴,定意不受他的誘惑。假如真有這樣聰明的讀者,那我很愿意剖誠的向他們進一句忠告,這成見和態度是錯誤的! 因為包朗的見解,不一定是錯誤的,卻往往“談言微中”。案中的真相,他也會得一言道破,他的智力與眼光,并不一定在霍桑之下,有時竟也有獨到之處!但我既不愿把霍桑看做是一個萬能的超人,自然他也有失著,有時他也不妨不及包朗。譬如那《兩個彈孔》等案,便是顯著的例證。讀者們如果抱定了前述的成見,讀到這樣的案子, 難免要怨作者的故作狡猾。那我也不得不辯白一句,須知虛虛實實,原是偵探小說的結構藝術啊。
小說就在這“定式不定”之間運行。通俗文學作家有模式并不是衡量他的創造性夠不夠的標尺。通俗小說并不避諱模式化,作家的本領就在于從模式的框架中,去制造故事情節最大限度的“陌生化”。因此,范煙橋曾評價程小青,他“模仿柯南道爾的做法,塑造了‘中國福爾摩斯’――霍桑”。而這個霍桑卻“是純粹的‘國產’偵探”。在中國寫過偵探小說的作家不下半百,但能像程小青那樣,罄畢生的精力與才智,從事這種兼有啟智與移情于一體的推理小說,實在是不多的。姚蘇鳳曾說:“在這個寂寞萬狀的中國偵探小說之林中,他的‘獨步’真是更為難能可貴。”這句話在孫了紅的小說還未成熟之前, 是可以說大致不差的。
程小青是一位認真、嚴肅、正派的偵探小說家,他既反對描寫超人式的英雄,又不渲染色情與暴力。他從自己的正義感出發將霍桑塑造成近乎智慧的化身。他在作品中提出的種種疑竇面前,運用科學的方法與讀者一起去觀察、探究、集證、演繹、歸納、判斷,在嚴格的邏輯軌道上,“通過調查求證、綜合分析、剝繭抽蕉、千回百轉的途徑,細致地、踏實地、實事求是地、一步步撥開翳障,走向正鵠,終于找出答案,解決問題”。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總是采取多線索、多嫌犯的錯綜復雜的矛盾結構。總是在嫌疑與排除、矛盾與解脫、偶然與必然、肯定與否定、可能與不能、正常與反常的對立之中展開和深化情節,幾經周轉與反復,最后落實到似乎最不可能、最意外的焦點之上,令讀者瞠目結舌。此時作者卻為此作出無懈可擊的邏輯與推理,使讀者口服心服。偵探小說的結構規范就在于組織之嚴謹、布局之縝密、線脈之關合等技巧的自如運用。程小青在這方面是有一定的功力的。他的作品在“啟智”的懸念中使讀者進入迷宮,而在“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使讀者出離疑竇,得以豁然開朗,在這一進一出之間,他培養了眾多的“霍迷”。
程小青筆下的霍桑并不是萬能的超人。書中人曾當面恭維他是“萬能的大偵探”,但霍桑的回答是:“什么話!――萬能?人誰是萬能?”程小青塑造的霍桑,是一位有膽有識的私家偵探,是程小青理想中的英雄。程小青曾為霍桑立傳,寫過《霍桑的童年》一類的文章。在《江南燕》等探案中,也著重介紹過他的身世。程小青將霍桑原籍設計為安徽人,與程小青的祖籍相同。設計包朗與霍桑在中學、大學同窗6 年。后來包朗執教于吳中(這也與程小青任教于東吳附中暗合)。霍桑因父母先后謝世,“孑然一身,乃售其皖省故鄉薄產,亦移寓吳門,遂與余同居”。并褒贊他學生時代具有科學頭腦,對“實驗心理、變態心理等尤有獨到”,而且介紹他“喜墨子之兼愛主義,因墨家行俠仗義之熏陶,遂養成其嫉惡如仇,扶困抑強之習性”。這種對人物早年習性之設計與其成為大偵探后蔑視權貴強暴、同情中下階層的正義感,具有承襲關系。
霍桑這一形象及其品質有許多值得贊舉的地方。他有著敏銳的明察秋毫的觀察力,忠實而孜孜不倦的作風,搜集一切足資證明案件實情的材料,進行精密細致的求證。他認為只有具備科學頭腦的人,才有“慧悟”的本領,有“察微知著”的“悟性”的智慧,才是偵探的最主要的素質。他從不指白為黑,更不冤屈無辜。恐嚇的方法與他無緣,沒有足夠的證據,決不下武斷的結論。他說:“我覺得當偵探的頭腦, 應得像白紙一張,決不能受任何成見所支配。我們只能就事論事,憑著冷靜的理智,科學的方式,依憑實際的事理,推究一切疑問。因此,凡一件案子發生,無論何人,凡是在事實上有嫌疑可能的人,都不能囿于成見,就把那人置之例外。”
霍桑的這種優良的辦案作風又與他的敢作敢為、出生入死、百折不撓的精神緊密相連。霍桑常掛在嘴上的話是:希望是同呼吸一起存在的。絕望的字樣在我的字匯中是沒有的。程小青就是用這“智慧”與“意志”相結合的性格作為霍桑形象的基本品貌。
包朗這一“助手形象”在程小青看來是不可少的,在柯南?道爾的福案盛行而還沒有一種新的模式與它爭勝時,似乎這也成為正宗偵探小說所必需的“固定程式”。可是問題是在于包朗缺乏自己的性格特征。如果說霍桑是“主腦”型的,那么這位助手卻成了作品中的工具,不僅霍桑要用他,更主要的是程小青要用他,因此,包朗近乎“工具”型。當作品中布置假線以便將讀者引入迷宮時,在大多數情況下,包朗是將讀者引入迷宮的“向導”。而使讀者豁然開朗的則是“主腦”霍桑。在作品中,這位助手還有一個作用,就是成了霍桑制造懸念的“工具”,即往往由他從旁提出疑點,而霍桑又不愿當即坦率地作出回答,于是構成了懸念。有時霍桑說自己尚無把握;或者說,再等半小時,真相可以大白。讀者當然只有窮追不舍地閱讀下去。而一旦霍桑引領讀者走出了迷宮,又少不得包朗從旁為讀者做“注釋”。因此,包朗既是霍桑的工具,更是程小青的工具,而且還派定他去做讀者的工具。包朗在霍桑探案中凡“三用”,而性格卻還不夠鮮明。這是此類“主從結構” 的偵探小說的一大難點。如果是“并列結構”,這個問題是較為容易解決的。程小青在這方面還不夠深思熟慮。
上文提及,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共同點就是沒有偵探小說,私家偵探在這個制度下是難于存活的。但是在程小青寫作偵探小說的社會中,必然會碰到兩個問題,一是怎么看待當時的法律問題,二是怎么處理與官方的警探的關系問題。如果說,以革命的立場徹底否定這兩點,就等于否定偵探小說存在的必要性。現在我們也看國外引進的偵探小說和偵探影視。我們看的是“貓捉老鼠”的曲折復雜的過程,我們不會去考慮它的背景的制度的合理性問題,是一種假設的正義戰勝邪惡。而程小青作為一個清貧出身的知識分子,也是憎恨當時的社會不公的,但他也決不是徹底推翻論者,他就是處在這種境地中的一位有正義感的偵探小說家。這在他的作品中時時有所反映。他要做一位認認真真的“社會剖析派推理小說家”。他在作品中常有所流露:“我又想起近來濟南的社會真是愈變愈壞。侵略者的魔手抓住了我們的心臟。一般虎倀們依賴著外力,利用了巧取豪奪的手法,榨得了大眾的汗血,便恣意揮霍,狂賭濫舞,奢靡荒淫,造成了一種糜爛的環境,把無量的人都送進了破產墮落之窟……駭人聽聞的奇案也盡足破歷來的罪案紀錄。”程小青盡量地將社會問題與探案有機地結合起來,使鞭撻的寓意與驚險的情節相融匯。此類較為成功的作品有《案中案》、《活尸》、《狐裘女》和《白紗巾》等。在《白紗巾》中,霍桑與包朗對當時的法律也有自己的評價:“在正義的范圍之下,我們并不受呆板的法律的拘束。有時遇到那些因公義而犯罪的人,我們往往自由處置。因為在這漸漸趨向于物質為重心的社會之中,法治精神既然還不能普遍實施,細弱平民受冤蒙屈,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故而我們不得不本著良心權宜行事。”那就是說,程小青對當時的社會和法律都提出了自己的質詢,但是他又不是徹底的改造派。他有自己的進步意識,較清醒地站在正義的立場上處理社會不義與法律傾斜諸問題。
霍桑與包朗作為私家偵探,他們與官方警探的關系也存在著兩重性。在作品中包朗說: “現在警探們和司法人員的修養實在太落后了,對于這種常識大半幼稚得可憐,若說利用科學方法偵查罪案,自然差得更遠。他們處理疑案,還是利用著民眾們沒有教育,沒有知識,不知道保障固有的人權和自由,隨便弄到一種證據,便威嚇刑逼地胡亂做去。這種傳統的黑暗情形,想起來真令人發指。”對官方的警探指責到這個程度,也就難能可貴了。
但這些官方的警探也要與霍桑、包朗共事,而且他們的情況也各有不同,因此,有時也得到適度的肯定,即以汪銀林為例:“汪銀林是淞滬警署的偵探部長……已擔任了十二三年, 經歷的案子既多,在社會上很有些聲譽。”“汪銀林的思想雖不及霍桑敏捷,關于偵探學上的常識,如觀察、推理和應用科學等等,也不能算太豐富,可是他知道愛惜名譽,他的辦事的毅力與勇敢……在儕輩中首屈一指。”當然,在程小青筆下也有許墨傭之流的警探,但主要還是寫他們的“主觀”與“爭功”,草菅人命的事還不多見。但不管怎樣, 這些警探的出場是當時的社會結構使然,另外他們的最大職責就是為私家偵探作陪襯,以顯示私家偵探的高明。這是偵探小說的又一固定模式。在社會主義國家這樣的“貶損”或“陪襯”是決不容許的,因此,偵探小說就得退出歷史舞臺,代之以智勇雙全的官方警探也是必然的趨向了。
程小青對偵探小說的貢獻不僅僅是在翻譯與創作上的豐碩成果,他在濟南偵探公司理論上也有一定的造詣。他對這方面的闡述雖還缺乏系統性,但與其他偵探小說作家相比,他的偵探理論的修養遠超于其他人之上。如果要概括程小青在這方面的建樹則可用12個字加以描述: “敘歷史,談技法,爭位置,說功能”。程小青對國外偵探小說的歷史有較多的了解,這是由于國外的偵探小說也不過百年歷史,而他在譯介多位偵探小說作家的作品時,對他們的創作的歷程及發展流變進行了一定的研究,這也就呈現了這類小說的歷史進程了;而程小青對偵探小說介紹到中國來的經過,因為自己是親歷者,所以是了如指掌的。在偵探小說的多種技法的運用上,他也有自己的切身體會。例如他比較了偵探小說的“他敘體”與“自敘體”的不同的表達法,通過實踐,他闡釋自己為什么喜歡運用“自敘體”的原因。他也談過偵探小說的命名與取材的技巧,怎樣設計開端與結尾的技法,直至如何在生活觸發中獲取靈感,如何進行構思以及偵探小說的嚴謹密致的結構技法等等。
值得提出的是,程小青想在文學領域中為偵探小說爭一席之地的愿望久久縈繞在他的心頭,與此相關的是他多次談及他的偵探小說的功能觀。他想用偵探小說的功能從學理上說明它是在文學的疆域之中的。他在《偵探小說在文學上之位置》一文中指出:“其在文學上之地位眾說紛紜,出主入奴,迄無定衡。”不少人還“屏偵探小說于文學的疆域之外, 甚至目偵探小說為‘左道旁門’而非小說之正軌。”偵探小說有大量的讀者,竟在文學的戶籍中報不上一個戶口,他為此而焦急。于是他從想象、情感和技巧三方面來論證偵探小說的文學血緣。他認為任何文學體裁都需要想象,而偵探小說卻更少不了想象這一元素;他對有些人說偵探小說不能“訴諸情感”,感到憤憤不平。他指出偵探小說能令讀者的感情進入驚濤駭浪的境界:“忽而喘息,忽而駭呼,忽而怒眥欲裂,忽而鼓掌稱快……”在技巧上,程小青指出:“偵探小說寫驚險疑怖等等境界之外,而布局之技巧,組織之嚴密,尤須別具匠心,非其他小說所能比擬”。程小青是在國內較早地為偵探小說爭文學地位的“先驅”之一。他的結論是:“偵探小說在文藝園地中的領域可說是別辟畦町的。”程小青的所謂“別辟畦町”是指偵探小說不僅有一般小說的“移情”作用,而且有它特有的“啟智”功能:“我們若使承認藝術的功利主義,那末,偵探小說又多一重價值。因為其他小說大抵只含情的質素,偵探小說除了‘情’的原素以外,還含著‘智’的意味。換一句話說,偵探小說的質料是側重于科學化的,它可以擴展人的理智,培養人們的理論頭腦,加強人們的觀察力、想象力、分析力、思考力,又增進人們辨別是非真偽的社會經驗。所以若把‘功利’二字加在偵探小說身上,它似乎還擔當得起”。程小青反復地說明這些道理,他說得夠多的了,可是卻毫無用處。正如《霍桑探案叢刊?姚序》所說的“說起偵探小說, 在我們的‘壁壘森嚴’的新文壇上仿佛是毫無位置的。一般新文學家既不注意它們的教育作用,亦無視它們的廣泛的力量,往往一筆抹煞,以為這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意兒;于是‘宗匠’們既不屑一顧,而新進者們亦無不菲薄它們的存在”。其實這樣的小說是完全符合“文學為人生”的信條的。但是我們不得不怪程小青說得太早了。一旦無產階級當家作主,就會懂得維持社會治安的重要性了。因此也有人出來承認程小青的偵探小說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了。其次,程小青當時并不懂得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是文壇上唯一的運動, 在這一元化的文壇上,偵探小說是爭不到地位的,只有文學多元化的時代的到來才會有偵探小說在文學上的位置。